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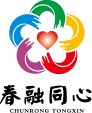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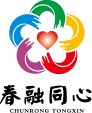
 首页>历史人文
首页>历史人文 魁阁者,呈贡古城村之魁星阁也,1940年初,为避日机轰炸,附设于云大的一个社会学研究室,迁到该阁。研究室为燕京大学和云大的合作机构,1940年10月,费孝通先生在燕大的业师吴文藻离开云大到重庆工作,研究室由费主持讨论和制定写作计划。费先生简称魁星阁为魁阁,久之,这个在魁星阁多年的研究室也就得了魁阁的绰号。本文篇名,脱胎于“魁阁小小,成绩多多”的赞誉。魁阁小,研究室也就前后十余人,但“成绩多多”,为国内外社会学领域同仁公认。吴文藻、费孝通及陶云逵、张之毅等著名教授、学者,在小小魁阁里取得了探索中国社会发展及战后社会重建等问题的丰硕研究成果,竖起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学的一座里程碑。
凝望着魁阁小小的身影,我眼前浮现出同为三层,但体量约为魁阁两倍的滇中名胜大观楼。大观楼以濒临五百里滇池的绝佳地理位置,以孙髯翁大观楼长联而蜚声海内外。那个既没有使命感,也没有责任感的咸丰皇帝,曾为大观楼御题“拔浪千层”,算是在书法上露了一手。而长联,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并且是文章大家和杰出诗人的毛泽东主席,反复吟诵后赞之曰:“从古未有,别创一格”,世人亦誉之为“古今第一长联”,评价颇高。
离云南“首邑”中心不远,又居滇池要津的大观楼,其机遇,自然要比离市中心稍远的呈贡魁星阁好,因而建筑规模就明显大于魁星阁,因而得咸丰皇帝御题“拔浪千层”。其时魁星阁已建成三十多年,但皇上不一定知道此阁,魁星阁、魁星楼一类建筑较多,没有唯一性。而大观楼,占尽地利,极富地域特色,经孙髯翁登临此楼,披襟岸帻的一番吟咏,并刊刻成联,楼前高悬,高人韵士、迁客谪人,放眼五百里滇池,游目骋怀、畅叙幽情,数千年往事注上心头,感同身受,情不自禁地齐声喝彩。大观楼楼因联传,联因楼显,声名鹊起,相得益彰,终与黄鹤楼、鹳雀楼等名楼比翼齐飞。呈贡魁星阁虽然有典型的清代建筑风格、较高的古建筑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但“养在深闺人未识”。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家乡无人“大魁天下”:公元1321年,云南才首开科举,晚于中原715年。此后时断时续,到了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平定云南后,才有规模地兴起了滇学而持续地举行科考。云南在整个科举史上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至1903年废科举止,全国共产生599个状元,云南仅有一位经济特科第一名,更遗憾的是经济特科状元却花落滇南石屏,祈盼文运天开,祈求文化、教育、宗教兴旺和人才登魁的呈贡魁星阁诞辰近百年,呈贡还是未能大魁天下。然袁嘉谷虽系石屏籍,但十多岁就被选入昆明经正书院学习, 31岁在昆明为云贵总督魏光焘举荐赴京应试。袁的高中状元,是石屏的光荣,是云南的光荣,更是昆明的光荣,因此,昆明将建于康熙初年的魁星楼,改称“状元楼”。该楼于1900年重建时,因感魁星楼名称还不能表达愿望,更名为“聚奎楼”,意即“斯楼成,魁星聚。”苍天有眼,重建该楼仅三年,袁嘉谷便“魁星占鳌”,实现了包括呈贡人在内的昆明人的愿望!呈贡人在欢欣鼓舞兼带遗憾之余,大受启发,于1922年重修了呈贡魁星阁。
由于经费紧张,重修较马虎,18年后魁星阁内部已陈旧不堪,地板踩上去嘎吱发颤,晃晃悠悠,让人担心薄薄的地板会断裂或松动脱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三层小楼,楼上住人,楼下研究讨论,居住面积不大,研讨环境亦显拥挤狭窄,但费孝通还是相中了魁星阁,魁星阁也就迎来了追赶昆明状元楼的机会。很多学者对魁阁的工作团队和学术气氛发出由衷的赞叹,费正清说:“费孝通是头儿和灵魂,他似乎有把朝气蓬勃的青年吸引到他周围的天赋……他的创造性头脑,热情、好激动的性格,鼓舞和开导着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反过来,他们同志友爱的热情,生气勃勃的讨论,证实了他们对他的信任和爱戴。”费孝通自己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活的,不会忘记的。”
尽管物质匮乏,生活条件简陋,魁阁的墙缝和椽柱里躲着虱子,夜晚叮得人难于入睡,但魁阁的学术团队从基地出发,深入乡村地头、农田茅舍,不仅仅从结构形态、手工业、农业的发展状况来认识乡土中国,更从文化的层面加以观照:中国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是魁阁学术团队社会调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费主持的魁阁,陶云逵、张之毅、许烺光、史国衡、田汝康、林耀华、谷苞、胡庆鈞、瞿同祖等一批青年才俊、社会学者,调查、研究、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讨论、总结中国社会学和战后中国重建等学术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费孝通一人的研究成果就达119部(篇),以其1943年赴美讲学翻译改写的《乡土中国》和《云南三村》(与张之毅合著)尤为重要。经过大量深入的农村调查,经过“尊重真知,不树权威,坦诚平等,各抒己见,和而不同”的讨论,形成了魁阁精神,它的特点是:“研究工作的开创性;学术领袖的个人魅力;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有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自愿结合;有一定时间的持续性;学者正处在学术最佳年龄段。”又有学者归纳为四个特征:“自由研究;尊重个人;公开辩论;伙伴精神。”在魁阁的研究团队中,除吴文藻年龄稍大,离开魁阁较早,其余在魁阁研究时间长的学者中,均符合上述对魁阁精神的总结。魁阁学术团队可谓“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又有 “绣罢鸳鸯从君看,又把金针度与人”的学术气度和个人魅力。费与陶云逵争论最多,常常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陶曾经回忆说:“我们不是没有辩得不痛苦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会。”费也说:“在和云逵相处的四年中,我实在领会到‘反对’的建设性。”
魁阁团队的一大批学术成果,加上吴文藻早年及费孝通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的论文《江村经济》,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里程碑。魁阁终于扬眉吐气,魁星占鳌。
魁阁小小,成绩多多,感慨滔滔。费孝通先生能够带领他的团队,在社会学暨民族学领域大魁天下,又一次证实,人须先立定志向,然后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去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矢志不渝,壮志前行,才能有所作为。因为生活艰辛,工作繁重,陶的爱子不幸夭折,年仅40岁的他也英年早逝。这位中国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西南边疆社会研究的拓荒者,是一位拼命硬干的人,是民族的脊梁。“几处芦笙呜咽鸣”,“一度追怀一怆情”,爱国学者们长歌当哭,哭后益坚,掩埋好同伴尸首,擦干眼泪,不坠青云之志,又全身心投入了开创性的研究,终得夺魁,令我等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的学生,不好意思为自己的无成就、少成就推客观,此一感也。其二,要干大事,要有人才。费孝通先生和他的魁阁团队,有好几个人属于五四之后出国留学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对团队的年轻人有直接的影响,他们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志向,又通过“席明纳(seminar)”式的讨论,具有了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及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成为极富创新精神的新一代人才。有了这样的人才,才可能开创新的科学领域,在另一意义上“大魁天下”。其三,正如很多人感慨的那样,几乎每个成功的男人身后都站着一个优秀的女性。费的身后站过他的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王同惠,与费孝通皆师从吴文藻教授,师出同门,志同道合。王同惠性格温婉和蔼、面容白皙、聪明大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才貌冠群芳。这一对天作之合,竟然完美到让老天都先挺后嫉,他们短暂的108天婚姻,戛然终止在他们为共同的事业赴广西中部大瑶山的考察中,在大瑶山,费误落猎人捕兽的陷阱,王为救费,呼救奔走,不幸落入深涧身亡,为所爱的人献身,死得悲壮而浪漫。而为共同追寻中国社会学之理想和事业的献身,其悲壮色彩,其理性的浪漫,已然超过了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笔下那个为所爱的人而献身的,可爱的契尔凯斯族姑娘,为人间一千古绝响。我想当老天亲见这位“纯洁之美的精灵”殉难时,他也会为中国社会学失去一才女追悔流泪的。
但立志为中国社会学奉献的费孝通,并没有“在绝望的忧愁的折磨中”屈服,他挺过来了,三年后的1939年有了第二任妻子孟吟。费与孟由此开始了另一段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生活。一天,当费像往常一样,搀扶着怀孕的妻子在古城村边桉树林里散步时,日本轰炸机突然飞临,炸毁了他们赖以栖身的农家小屋,这一惊吓,使得怀孕9月的孟吟突然感到腹部一阵巨痛,就要分娩了。而呈贡一带的农村风俗,谁家的孩子在谁家生,接纳别人家的孕妇在自己家里生孩子会倒霉,因此没有人敢接纳夫妻俩。折腾到子夜时分,一位善良的广东牙医才帮忙把孩子生下来。经过大瑶山和这次日机轰炸下生孩子的生死磨炼,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作为妻子的孟吟,对家庭和责任的认识有了又一次质的飞跃。
费孝通后来慨叹:“云南是我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所以我把云南(具体指呈贡)当作我的第二故乡。”他的学生看着夫妻俩共担一桶水、同劈一堆柴、你拣菜我做饭、饭后夫妻相伴同带孩子游戏的家庭生活感慨:“费先生有一位贤惠的师母,对费先生异常体贴,膝下儿女成群,都很乖巧,家庭的美满大概也给费先生一个好的工作心情。”的确,费一生的成就和这两位夫人是分不开的。
其四,有人感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不?“费老已乘仙鹤去,此地空余魁星阁。”今年9月,仙逝的国宝级大师汤一介老先生,就多次要求不要称他为大师。在他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当今也没有大师。的确,大师的称号不是随便就可以封的。世代书香,约10亿字的《儒藏》总编纂汤一介老教授,没有泰斗级的水平,怎敢出任此职?我们应该有现今的大师,“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嘛!新时代更是迫切地呼唤出新的大师。新时代要求,随着时代前进,知识不断创新。而知识的创新,必须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或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做到。这就需要建设一流的大学,培养一流的创新型人才。
而云南作为一个后开发地区,本土名人和大师相对较少。为将来彻底解决云南高教规模小、发展慢、与一流大学相比差距较大的问题,省委、省政府在《关于深化改革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决定》中要求,通过5年努力,使全省高教水平和竞争力进入西部省区先进行列。将10所在昆高校集中到呈贡办学,有利于扩大规模,广揽人才,以形成新型工业、科研、文教园区。迁建一个教育、科研、文化的殿堂,更有利于集中力量,互相协调,齐心协力,资源共享,出人才、出成果、出大师。
呈贡是全国知名的菜乡、花乡、果乡。“呈贡蔬菜”名扬海外;“斗南花卉”香飘五洲;“呈贡宝珠梨”闻名遐迩。呈贡因彝语音译得名,意为盛产稻谷的湖畔坝子,而不是呈献贡品的意译。音译也好,意译也好,都说明呈贡是个好地方。呈贡文化底蕴也很丰富,享有“滇戏窝子”、“花灯之乡”的美誉,火把节唱山歌对调子的传统节庆活动,已发展成花灯、滇戏、山歌、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本土饮食文化、休闲观光等多种形式和内容的文化节。呈贡不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名至实归。呈贡新区是现代新昆明“一湖四片”布局中首先开发的热土,具有新城的区位优势和将来实现跨越式发展,助推面向拥有21亿人口的东南亚、南亚“桥头堡”战略的后发优势,有望建成西部乃至全国的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宜居都市。
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费孝通选择了魁星阁,“与文星共处连年,又听阁外春荷滴雨,声声入梦。聚学者相研一室,长忆灯前赤面争言,缕缕随风。” 在120多年的等待中,魁星阁终于迎来了费孝通及他的社会学团队,费后如“他乡遇‘故知’,两眼泪汪汪”,亲切地替朋友改名“魁阁”。如果说费孝通这位蜚声国际的学者,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标志性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呈贡魁阁则是这传奇中灿烂的一页。社会系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师生必须与社会紧密联系,必须经常在外进行社会调查,调查之后讨论、研究、分析、写出调查报告,因此魁阁、呈贡、昆明、云南,从中心向外围扩大,都是魁阁团队成长的土壤和空间。现今,这土壤和空间的条件比原来好得多,呈贡大学城渴望着能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采选到优良种子,经过悉心培育,结出累累硕果。
不必惆怅“仙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我们对呈贡,对呈贡大学城,充满希望和信心,因为小小的魁阁,就曾出过多多的成绩,“此是光辉史一页”,激励后人超前人。(民进昆明市委投稿)